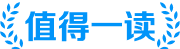问道手游照妖镜在谁手上
问道拿照妖镜的是谁?
一、在《西游记》中,拿照妖镜的是托塔李天王。当唐僧师徒路过小雷音寺时,遇到了黄眉老怪,孙悟空无法战胜他。于是,他们向天庭求助,托塔李天王带着照妖镜前来助阵。他用照妖镜照出了黄眉老怪的原形,最终帮助孙悟空战胜了妖怪。
二、有照妖镜的的人是云中子,位置在木系师门。
问道手游里谁有照妖镜?
古代封神斗法托塔李天王李靖
胡适为何认为京剧和律诗都是下流的?
一、胡适在警示后人,与其在艰难中负重前,倒不如轻装上阵。我们必须和世界赛跑,假如落伍,等待我的是所有的灾难和痛苦。而不是幸福与平安的降临。落后的文字,将束缚人们的思想与创新。
二、民国时期的文人灭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多笑话。灭传统文化,必然产生军事统治,早在18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哲学证明,日本明治维新就掉进了这个坑里,导致日本的军国主义。民国的文人还灭汉字呢,民国文人给传统文化捏造了一个愚民的罪名,导致最后蒋家王朝。传统文化是一国的精神食粮,抽空精神食粮会导致精神危机,如以低俗为道德高地,以暴力为真理余威。法国大革命就是因为灭传统文化,导致了深重的灾难,柏克等哲学家都有论述。一个国家的人民各自选择什么样的文化为精神食粮,是一个生态平衡系统,强行干涉损毁这个系统,必导致灾难。保护传统文化如今是全世界的文化潮流和良心工程,所以各国都竞相申遗。
三、胡适认为"京剧与律诗都是下流的",我以为此言更"下流"。何为"下流",一是内容庸俗,二是行为下作。京剧和律诗"都""下流",无证据,既然无证据,只能说胡适出言下作下流。不过胡适也作过"下流"的律诗,水平极下等无水平,也不知胡适靠什么出名?鲁迅说胡适不过有个美国文凭而巳。
四、胡适为何认为京剧和律诗都是下流的?
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胡适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就简单地认为他所说的话、他的“学术”观点是正确的,不能仅凭他一家之言,就相信他的观点。
我个人偏激、偏见、狭隘地认为:胡适是因为民国时期留学西洋,“崇洋媚外”,被西洋文化“洗空了大脑”,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华文化的京剧和律诗错误、错判的认识、认知………
京剧和律诗:都是中华文化当中的杰出精华、精髓,都是国粹、国魂和国宝………
五、五四时期,文学先辈反对八股,提倡白话无疑是对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把古典诗词一起反掉就有点象倒洗澡水把孩子一起倒那样矫枉过正了。历史是最公正的,古典诗词现在仍然被大众喜欢着就证明了这一点。但胡适说的一些今人写古诗词三个毛病:一、言之无物,二、摩仿古人,三、无病呻吟,却也是一针见血。其实现在一些人写新诗何尝沒有这三个毛病:一、言之无物,二、摩仿翻译腔,三、无病呻吟。总之,诗是心的表达,语言要美,粗话脏话成不了诗,心要真诚,为诗而诗,会有文字游戏之感。现在的赛诗玩诗,我不反对,但把这作为方向,一窝蜂,是不是又偏了。诗的生命力在于社会、时代、大众。唐诗的生命在于写了唐代的人,宋词的生命在于写了宋时的人。当时的时代成了我们现在的历史,我们的时代将是未来的历史。如果我们现在写的诗体现不出时代感,将来是不会有什么价值的。
六、罗尔纲《师门五年记》收有梁实秋一篇写胡适的文章,梁文记载了胡适曾在某所大学的演讲,“他在讲词中提到律诗及平剧,斥为‘下流’。听众中喜爱律诗及评剧的人士大为惊愕,当时面面相觑,事后议论纷纷。我告诉他们这是胡先生数十年一贯的看法,可惊的是几十年后一点也没有改变。”
若是按照梁文的记载,胡适说的是“律诗及平剧”“下流”,而不是“京剧”。
但梁实秋表达了与胡适并不相同的看法,“中国律诗的艺术之美,评剧的韵味,都与胡先生始终无缘。八股、小脚、鸦片,是胡先生所最深恶痛绝的,我们可以理解。律诗与平剧似乎应该属于另一范畴”。胡适说律诗“下流”,大师有时候的作为,总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甚至理性儒雅如胡适。
律诗是胡适真不喜欢的一个古典存在,甚至是敌视。如果要问胡适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中国古典文学形式?骈文以外,那就是律诗了。非常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律诗与骈文所容纳的都是最高浓度的文言酒精,这不能让胡适走近与喜欢。
胡适对律诗有多种描述方式,但无一例外,全都是贬抑。
在《白话文学史》中,作为与白话最大的对立面,胡适集中表达了对于律诗的恶感。在胡适看来,律诗是无意义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律诗本是一种文字游戏,最宜于应试,应制,应酬之作;用来消愁遣闷,与围棋踢球正同一类。老杜晚年作律诗很多,大概只是拿这件事当一种消遣的玩艺儿”。
同时胡适又认为律诗所写只是“难懂的诗谜”,并且认为律诗之路是“死路”,“《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这些例子都可以教训我们:律诗是条死路,天才如老杜尚且失败,何况别人?”胡适甚至认为律诗是一种“罪孽”,“律诗的造成都是齐梁以至唐代的爱文学的帝后造作的罪孽”。
律诗是“罪孽”的思想,在胡适1934年所写《再论信心与反省》中有了进一步的发挥,“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沉重”,“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向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律诗似乎已是“罪孽沉重”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把律诗与八股放在一起,都不免是对律诗的极大折损,而把律诗与“小脚”、“太监”、“姨太太”相提并论,这对律诗的羞辱应该是空前的了。
但不管怎样,律诗总是一种有门槛有难度的一种艺术存在,而且对现代人来说,这种难度还不低。那么如何削平这个难度呢?
胡适也有办法。吴稚晖早先就有“文言比白话容易”论,他这样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这是要抓住古典性事物的一招之错,予以现代性的捷径超越,这包含有对古典性事物的蔑视与不屑,而且这种语言表达上的超越似乎就是真的超越了。
胡适在吴稚晖的影响与启发下,他也有对律诗的“超越”方式。胡适在《四十自述·在上海之二》写道:“做惯律诗以后,我才明白这种体裁是似难而实易的把戏,不必有内容,不必有情绪,不必有意思,只要会变戏法,会搬运典故,会调音节,会对对子,就可以诌成一首律诗。”
律诗真的有这么好做吗?连一贯热爱自己老师的苏雪林也表示不信。苏雪林在《我与旧诗》中反问道,“可是,律诗这把戏正像胡先生所说并不难玩,说来谁也不会相信吧?”上过家塾、学过“对对”、做过排律的苏雪林,深知做律诗的甘苦,不得不挺身反对自己老师的说法。
王元化也不同意胡适的这种说法,他在1993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读胡适《四十自述》。偶然想到:律诗格律与戏曲程序乃同一性质。胡适称律诗最宜作没有内容的应酬诗。这固然是对的,但不能因此将格律诗都视为言之无物。同样道理:戏曲演员固然可以借程序在演技上敷衍塞责,但也可以通过程序去进行艺术性创造,表现个性特征”。
律诗当然可以“诌”,但不代表所有律诗都是“诌”;亦不能因为律诗有“诌”的可能,就断然堵住通往律诗之路。律诗可以“诌”,但不能用“诌”抹煞一切律诗,但也不能否认古典律诗曾产生了大量的杰作。
律诗难做,做好律诗又是谈何容易?从严羽到袁枚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严羽有“律诗难於古诗”之说,方东树亦有“七律为最难,尚在七言古诗之上”的观点。
袁枚也有经验之谈,“作古体诗,极迟不过两日,可得佳构;作近体诗,或竟十日不成一首。何也?盖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而近体之妙,须不着一字,自得风流,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
“尝以诗词为中土文艺之精髓”的朱光潜,是以中国古典诗歌为傲的。他认为“中国过去的文学,尤其在诗方面,是可以摆在任何一国文学旁边而无愧色的”。朱光潜在三十年代初,曾写有《诗论》为诗的音律和律诗的产生辩护;到了四十年代末,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发表《现代中国文学》时,也没有忘记为古典诗歌再作辩护。
尽管顾颉刚说胡适“澈骨聪明,追攀不上”,但不得不说,胡适与最具中国韵味艺术形式是有“隔”的,说是“隔膜”也可,说是“隔阂”亦无不可。
李敖说“胡适不是好的文艺批评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说胡适对于《红楼梦》吧,可以说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其在对于《红楼梦》的“国故整理”上成就卓著。但胡适对于《红楼梦》艺术世界则绝不感冒,对于《红楼梦》艺术水准评价更是低的离谱。
胡适在写给苏雪林的信中说,“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是过分赞美《红楼梦》了。《红楼梦》的主角就是含玉而生的赤霞宫神瑛侍者的投胎;这样的见解如何能产生一部‘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小说”。与其他古典名著相较,《红楼梦》艺术地位如何呢?“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答苏雪林书》)。
这只能说胡适与红楼所构筑的审美世界是无缘的。胡适在六十年代与高阳书信中,亦表达了类似观点。无独有偶,陈独秀对《红楼梦》也是评价不高,他在1917年8月1日写给钱玄同的信中,表达了对于《红楼梦》的“讨厌”。
尼采认为拜伦的《曼弗雷德》高于歌德的《浮士德》,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认为,尼采的“判断力变得十分可怜”。在这个问题上,胡适认为《老残游记》这类的小说高于《红楼梦》,亦是如此。大师往往并不是十项全能冠军,他们也是有盲区的,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如鲁迅所说,名人的话并不总是名言。
再如对于中国的传统戏剧,胡适基本上是全盘否定的。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认为,“居然竟有人把这些“遗形物”——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当作中国戏剧的精华!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了”,“再看中国戏台上,跳过桌子便是跳墙;站在桌上便是登山:四个跑龙套便是一千人马;转两个弯便是行了几十里路;翻几个斤斗,做几件手势,便是一场大战。这种粗笨愚蠢,不真不实,自欺欺人的做作,看了真可使人作呕!既然戏台上不能演出这种事实,又何苦硬把这种情节放在戏里呢?”那些最具中国韵味的艺术形式,在胡适眼中,都变成了应该被淘汰的“遗形物”,夫复何言?
无怪乎李敖要说胡适“不懂中国旧戏的审美特点”了。相较而言,周作人则显现出更多的自反精神。《新青年》时代的周作人也是很反对旧剧的,但几年过后,周作人就对自己当年激烈的举动作了调整。周作人写道,“四五年前我很反对旧剧,以为应该禁止,近来仔细想过,知道这种理想永不能与事实一致,才想到改良旧剧的办法”,“旧戏的各面相可以完全呈现,不但‘脸谱’不应废止,便是装‘蹻’功能‘摔壳子’之类也当存在,中国旧剧有长远的历史,不是一夜急就的东西,其中存着民族思想的反影,很足供大家的探讨”。
周作人最后提醒道,“艺术的统一终于不可期;只千万不要想兼得二者,这是最要紧的事”。但在现代中国,想做“艺术的统一”之梦的,大有人在。
二十年代中期,闻一多曾为律诗打抱不平,因为当时的闻一多正在倡导“新格律诗”,他的“新格律诗”主张被时人认为有“复古”的嫌疑。
闻一多愤愤不平质问道,“做古人的真倒霉,尤其做中华民国的古人”。“我真不知道律诗为什么这样可恶,这样卑贱!”(《诗的格律》)但闻一多对律诗是相当看重的,当年曾“指导”郭沫若,要其“细读律诗”,以“中国艺术之特质,以镕入其作品中”,才会使自己的诗作大有改观(《律诗的研究》)。
胡适为什么会拒斥那些具有中国韵味艺术形式呢?苏雪林在《胡适的〈尝试集〉》中是这样解释的,“他是个实验主义者,一切不合科学精神之物,均在排斥之列”。这个解说还是有道理的。
对于中国的古典事物,胡适准备了两张网。凡是能被这两张网“打捞”上来的,胡适就予以肯定,凡是“打捞”不上来的,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了。
这两张网一张是“白话”,一张是“科学”。在文学史上,只要是与“白话”有些关联的,就都能得到正面肯定,哪怕是杜甫的有些诗;而“整理国故”正是为“科学”那张“网”建立的平台,比如“国故”中的“清学”,因其所用考据方法在胡适看来含有“科学”质素,因而会被胡适所肯定与关注。
而“律诗”与“骈文”既离白话很远,同时又是不能被“科学”界定的领域,因而被胡适厌弃,也就是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参考文献: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
严羽《沧浪诗话》
方东树《昭昧詹言》
朱光潜《诗论》
李敖《胡适研究》
问道中谁有照妖镜探查过常昊?
修行领任务那个人,跟随主线任务就行。